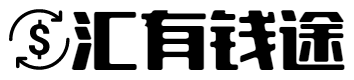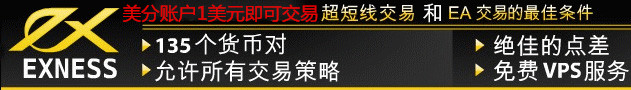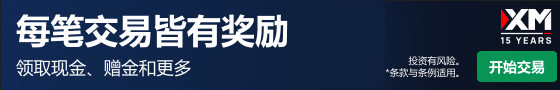探寻人工智能泡沫的经济基本面
 |  |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建设半导体工厂和数据中心的热潮,以满足大型语言模型的巨大能源需求。但随着投资猛增和估值飙升,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金融投机的增长速度已超过了生产力的提升。
近几周来,“我们正在目睹一场人工智能泡沫这一观点已从公众讨论的边缘走向主流。正如《金融时报》评论员凯蒂·马丁(Katie Martin)恰如其分地指出的那样,“到处都在谈论泡沫。”
这场争论因数据中心及支撑生成式AI的大型语言模型(LLM)训练与运行所需的庞大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激增而愈演愈烈。与此前的投机泡沫类似,不断攀升的投资规模推高了估值,两者在公开和私募市场均创下历史新高。所谓的"七巨头"科技企业:Alphabet、亚马逊、苹果、Meta、微软、英伟达和特斯拉——主导着标普500指数,每家公司市值均突破1万亿美元,其中英伟达更成为全球首家市值达5万亿美元的企业。
私募市场上,据传OpenAI计划从后2008时代最狂热的投资者软银集团募资300亿美元,估值高达500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融资推进之际,该公司2024年虽实现37亿美元营收但亏损了50亿美元,且预计到2029年总现金消耗将达1150亿美元。
与以往的投机周期相似,本轮周期的标志是创新性融资机制的涌现。四个世纪前,荷兰郁金香狂热催生了花卉球茎期货合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则是由合成型债务抵押债券和信用违约互换等奇异衍生品助燃。如今,类似的动态正在连接芯片制造商(英伟达、AMD)、云服务商(微软、CoreWeave、甲骨文)与OpenAI等大语言模型开发者的循环融资生态中上演。
尽管AI泡沫的轮廓已清晰可辨,但其实际影响将取决于它是否会从金融市场蔓延至更广泛的经济领域。这种转变将如何发生,乃至是否会发生目前仍不明朗。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数十亿美元AI基础设施项目官宣。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报告显示AI的商业应用回报令人失望,表明炒作可能已远超实际效果。
泡沫幽灵的往昔
金融泡沫可从其焦点与发生领域来理解。焦点关乎投资者押注的对象:那些吸引投机的资产在大规模部署时,是否具备提升经济生产力的潜力?发生领域则指这类活动主要集中于股权还是信贷市场。正是由债务驱动的投机行为,在泡沫不可避免地破裂时导致经济灾难。正如莫里茨·舒拉里克与艾伦·M·泰勒所揭示的,过去一个半世纪里,杠杆助推的泡沫屡屡引发金融危机。
2004至2007年的信贷泡沫便是明证,它以房地产为核心,最终酿成2008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这类泡沫毫无提升生产力的可能,其破裂时的经济后果极其惨烈,迫使以美联储为首的机构史无前例地为私人损失提供公共担保。
相比之下,20世纪90年代末科技泡沫的焦点在于全球范围内构建互联网的物理与逻辑基础设施,同时伴随着商业应用的第一波实验浪潮。这一时期的投机活动主要集中在公开股票市场,部分外溢至可交易垃圾债券市场,整体杠杆水平仍保持有限。当泡沫破裂时,造成的经济损害相对温和,通过常规货币政策便得以轻松化解。
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正是由一系列此类"生产性泡沫"所定义。从铁路到电气化再到互联网,金融投机浪潮反复调动大量资本,用以资助那些回报无法预先确定的潜在变革性技术。
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中,那些构建基础设施的公司最终都破产了。投机性资金使他们得以在反复试验催生出经济上可行的应用之前多年就开始建设。然而,没有人拆除铁轨、拆解电网或挖出地下光纤电缆。这些基础设施保留了下来,随时准备支撑想象中的“新经济”的创建,尽管经历了痛苦的延迟,且大多由新的参与者主导。发现这些“通用技术”所催生的“杀手级应用”所需的实验需要时间。那些期望从大语言模型(LLMs)中立即获得满足感的人很可能会失望。
例如,美国第一条铁路的建设始于1828年,而作为该领域杀手级应用的邮购零售业,则始于1872年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创立。十年后,托马斯·爱迪生通过点亮珍珠街发电站开启了电力时代,但电气化带来的制造业生产力革命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真正显现。同样,从1876年奥托内燃机的发明到1908年亨利·福特的T型车,从1958年杰克·基尔比的集成电路到1981年IBM个人电脑的问世,都经历了一代人的时间。1972年首次展示了互联网的雏形:亚马逊和谷歌则分别成立于1994年和1998年。
人工智能泡沫在这波浪潮中处于何种位置?尽管目前大部分投资来自科技巨头的庞大现金储备和持续现金流,但杠杆迹象已开始显现。例如,较晚加入这场竞赛的甲骨文公司,正通过约380亿美元的债务融资来弥补其相对有限的流动性。
而这可能只是开端。OpenAI已宣布计划在未来五年投入至少1万亿美元。考虑到如此规模的支出必然需要大规模举债,大语言模型只有短暂的时间窗口来证明其经济价值,并为这种超常投资水平提供合理依据。
早期研究给出了乐观理由。斯坦福大学的Erik Brynjolfsson与麻省理工学院的Danielle Li、Lindsey Raymond针对客服中心引入生成式AI的研究发现,AI辅助使员工生产率提升了15%。其中经验不足的员工获益最大,其工作效率提升超过30%。
Brynjolfsson及其合著者还观察到,遵循AI建议的员工效率逐渐提升,接触AI工具带来了持久的技能进步。此外,客户对AI辅助的客服人员态度更为积极,满意度更高,且要求转接主管的请求更少。
然而,整体情况似乎不太乐观。麻省理工学院的NANDA项目近期调查发现,95%的私营领域生成式AI试点项目均告失败。尽管该调查不如Brynjolfsson的同行评审研究严谨,但结果表明大多数企业对生成式AI的尝试未达预期。研究人员将失败归因于“学习鸿沟”:少数企业获得了专家协助,将AI应用定制于实际业务需求(主要是后台行政任务),而其他企业则试图自主开发面向外部职能(如销售与营销)的系统。
生成式AI的局限
生成式AI用户面临的主要挑战源于技术本身的特性。从设计上看,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会将训练数据(文本、图像和语音)转化为数值向量,再通过分析这些向量来预测下一个标记:音节、像素或声音。由于它们本质上是概率预测引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随机错误。
今年早些时候,已故的施乐公司传奇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前首席科学家布莱恩·坎特韦尔·史密斯精辟地指出了这一问题。爱丁堡大学教授亨利·汤普森转述了史密斯的观点:"(ChatGPT)说出错误内容固然不好,但真正无可救药的是,它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存在谬误。"
由此必然导致各类错误,其中危害最大的是"幻觉",听起来似乎合理,但描述的事物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正是语境至关重要的原因:在商业场景中,人们对错误的容忍度本就极低,当风险升高时更是趋近于零。
代码生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财务或运营敏感环境中使用的软件必须经过严格测试、编辑和调试。配备生成式AI的初级程序员能以惊人速度产出代码,但这些产出仍需要资深工程师仔细审查。正如网络上流传的众多轶事所示,一旦将测试和监督所需的资源考虑在内,前端获得的任何生产力提升都可能化为乌有。《堡垒》杂志的乔纳森·拉斯特说得很到位:
"AI就像中国的机器生产,它能以极低成本(这里以人类时间成本衡量)创造优质产出。这意味着当今的AI只是一个实用工具,仅适用于容错率高的任务。如果我让ChatGPT帮我研究某个主题,并将该研究融入我正在撰写的文章中,而结果只有90%正确性,那就有问题了。因为我的书面作品对错误的容忍度很低。”
剑桥大学经济学家黛安·科伊尔在其新书《进步的尺度》中指出了另一个主要担忧:AI的不透明性。"就AI而言,"她最近写道,"一些最基本的事实缺失或不完整。例如,有多少公司正在使用生成式AI?涉及哪些行业?它们将其用于什么用途?AI工具如何应用于营销、物流或客户服务等领域?哪些企业部署了AI代理,实际使用者又是谁?"
不可避免的清算
这就引出了核心问题:大型语言模型的价值创造潜力究竟如何?它们对计算能力和电力的无尽渴求,加上对昂贵监督和错误纠正的依赖,使得盈利前景充满不确定性。企业客户能否产生足够的盈利收入,以证明在基础设施和人力支持方面的必要投入是合理的?若多个LLM的性能趋于同质化,其输出是否会沦为大宗商品,使得token生产变成低利润业务?
从铁路、电气化到数字平台,历史表明,提供首个服务单元总是需要巨额前期投资,而每增加一个单元的边际成本会迅速下降,甚至低于回收初始投资所需的平均成本。在竞争环境下,价格往往向边际成本靠拢,导致所有参与者都在亏损运营。其结果,借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表述,总是一次次催生受监管的垄断企业、卡特尔或其他"限制贸易的共谋"。
企业级LLM部署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替代方案。其一是开发小型语言模型,这些系统基于精挑细选的数据集训练,专门用于完成特定明确的任务。摩根大通等大型机构或政府部门可以构建符合自身需求的垂直应用,从而降低幻觉风险并减少监管成本。
另一个选择是消费市场,AI供应商在此与老牌社交媒体平台争夺用户注意力和广告收入。在这个以娱乐性和参与度衡量价值的领域,一切皆有可能。据报道,ChatGPT拥有8亿"周活跃用户",是2月份时的两倍。OpenAI似乎准备乘胜追击,推出搭载LLM增强功能的网页浏览器ChatGPT Atlas。
但考虑到谷歌和苹果的浏览器均免费且已集成AI助手,尚不清楚OpenAI能否维持可行的订阅制或按次计费模式,以证明其巨额投资的合理性。多方估算显示,目前仅有约1100万用户(约占总数的1.5%)以任何形式为ChatGPT付费。因此,面向消费者的大型语言模型可能注定要在已经成熟的市场中争夺广告收入。
这场持续的竞赛结果难以预料。大型语言模型最终能否产生正向现金流,并覆盖其大规模运行所需的能源成本?还是说,仍处于萌芽阶段的人工智能行业将分裂成由专业小众供应商拼凑的格局,同时大型公司与其企业投资者所拥有的社交媒体平台展开竞争?当市场意识到这个行业正在分化而非整合时,人工智能的泡沫就将破灭。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更早的清算可能对整个生态系统有利,尽管对那些在顶峰入局的人来说将是痛苦的。这样的通缩能避免当今许多雄心勃勃的数据中心项目沦为闲置资产,就像过去泡沫遗弃的废弃铁轨和闲置光纤一样。从金融角度看,它还能阻止一波高风险借贷,避免再次引发杠杆泡沫和崩盘。
最有可能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生产力的泡沫只有在当前投机狂热冷却多年后才会出现。正如高德纳技术成熟度曲线所示,“幻灭的低谷”先于“生产力的高原”。时机或许并非人生的一切,但对投资回报而言,它几乎就是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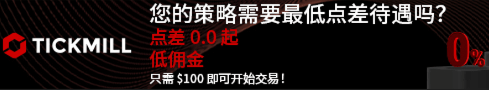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