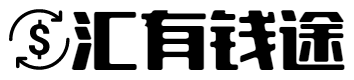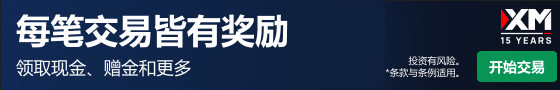如果耶稣诞生于今日,他在美国的遭遇会是什么样
 |  |
当天使的歌声消逝,当天空中的星子隐去,当国王和王子们归家,当牧羊人带着羊群返回,圣诞节的工作便开始了:寻找迷途之人,治愈受伤之人,喂饱饥饿之人,释放囚徒,重建国家,让人民和睦相处,在心中奏响乐章。----霍华德·瑟曼,神学家及民权活动家
每年圣诞节,基督徒都会庆祝一位诞生于压迫之下的婴孩:生于被占领的土地,生于政治恐惧的氛围,生于一个动辄镇压任何威胁其权威的事物的政府统治之下。
两千年后,其中的相似之处无可否认。
如果耶稣诞生在现代美国,在一个痴迷于监控、打击无证移民、宗教民族主义以及对国家元首绝对服从而非法治的政府统治下,他能否活到足够长的时间去宣扬爱、宽恕与救赎?他关于和平、仁慈及反抗帝国的讯息,是否会被贴上极端主义的标签?
尽管马槽中诞生婴儿的圣诞故事耳熟能详,但它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而言,也是一则警示故事。
罗马帝国本身就是一个警察国家,曾下令进行人口普查。约瑟夫和他怀孕的妻子玛丽前往小城伯利恒,以便登记在册。由于所有旅店都没有空房,他们只好住在马厩里,就在那里,玛丽生下了一个男婴,取名耶稣。由于得到政府要杀害这个婴儿的消息,耶稣一家带着他逃往埃及,直到安全返回故土。
然而,倘若耶稣晚诞生两千年会怎样?
假如耶稣不是降生于罗马的警察国家,而是此刻来到世间,他和他的家庭将受到何种对待?我们能否认出圣婴的人性,更遑论其神性?我们对待他的方式会与罗马帝国有所不同吗?若他的家人被迫逃离故土的暴力,前来我们的边境寻求庇护与避难,我们将为他们提供怎样的庇护所?
近年来,全国少数教堂提出了这些尖锐问题,并通过令人不安的逼真圣诞场景呈现了答案:耶稣与家人被隔离,分别关押在带刺铁丝网围顶的铁链栅栏内。
这些圣诞场景直指现代社会的软肋,耶稣诞生的故事本应从多维度警示世人:他的生平、教诲与十字架受难,已被党派政治、世俗主义、物质主义和战争所淹没,而这一切背后操纵的正是被称为"深层政府"的影子政权。
当代教会大多回避将耶稣的教导应用于战争、贫困、移民等现实议题。但值得庆幸的是,历史上总有人不断叩问自己与世界:耶稣会怎么做?
那位诞生于伯利恒、成长为游走四方的传道者与革命活动家的耶稣,那位不仅以死亡对抗当时警察国家(即罗马帝国),更用毕生向权贵直言、挑战时代桎梏、反抗罗马暴政的耶稣——面对当今世道的不公,他会如何作为?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曾自问耶稣会如何应对希特勒及其刽子手制造的恐怖。答案便是:朋霍费尔因试图瓦解纳粹德国核心暴政而被希特勒处决。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曾自问耶稣会如何对待苏联那些摧残灵魂的古拉格与劳改营。答案便是:索尔仁尼琴找到了自己的声音,用它揭露政府的压迫与暴行。
马丁·路德·金曾自问耶稣会如何看待美国的穷兵黩武。答案便是:金以"我的良知别无选择"为由,冒着举世谴责与生命危险,公开以道德与经济立场反对越南战争。
这些生命清晰地表明,"耶稣会怎么做"从来不是抽象命题。它始终关乎政治,充满危险,且代价高昂。
但这绝非神学模糊地带:耶稣对诸多事物的立场毫不含糊,慈善、悲悯、战争、暴政与爱更不例外。
耶稣并非生于安逸或安全之中。他出生贫寒,无栖身之所,身处一个被武力与恐惧统治的占领地,处于一个痴迷于控制、顺从和清除潜在威胁的政府监视之下。他的父母在政治上毫无权势。他的诞生之地简陋不堪。他生命最初的时光笼罩在对国家暴力的恐惧之中。
希律王听闻弥赛亚降生的消息后,并未心怀谦卑或反思,反而陷入偏执。仅仅因可能存在另一个权威的威胁,希律王便诉诸野蛮武力。这个教训历久弥新:暴政正是如此运作的。当不受约束的权力被不安全感支配时,总会试图消灭异见,而非直面自身的腐化。
现代政府,包括我们自己的政府,披着安全与"法律秩序"的外衣,行径却别无二致。任何对中央集权的挑战都被视为必须消除的威胁。在这样的环境中,向权力说真话是危险的。挑战帝国权威必将招致报复。
从降生那一刻起,耶稣就代表着一种威胁,并非因为他掌握暴力或政治权力,而是因为他的生命与信息揭露了帝国的道德破产,并提供了植根于正义、怜悯与真理的另一种选择。
耶稣成年后,道出了强大而深刻的箴言——这些言论改变了我们看待人的方式,挑战了帝国所代表的一切。"怜恤人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以及"要爱你们的仇敌",仅是他最具深度与革命性教导的几个例证。
面对当权者时,耶稣从不回避向权力诉说真相。事实上,他的教导动摇了当时的政治与宗教体制。这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最终被钉上十字架,作为对他人勿挑战当权者的警告。
你能想象吗?如果耶稣不是出生在罗马警察国家,而是在美国警察国家出生并长大,他的一生将会是怎样的境遇?
如果你愿意,试考虑以下情景。
若耶稣降生于美国警察国家的时代,他的父母便无需为人口普查跋涉至伯利恒。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将被录入庞大的政府数据库网络,被算法标记、分类、评分和评估,这些算法既不可见亦无法质疑。如今所谓的人口普查,早已不再是简单的人口清点,而是数据收割体系的一部分,为人工智能系统、预测性警务程序、移民执法和国家安全监视名单提供养分。
耶稣或许不会诞生于马槽,而是在家中降生。然而,代替东方智者和牧羊人献上礼物的,可能是这对父母不得不抵御国家社工的造访,这些官员会以家庭接生为由起诉他们。
倘若耶稣在医院出生,他的血液和DNA将在父母不知情或未同意的情况下被采集,并存入政府生物样本库。尽管多数州要求进行新生儿筛查,但越来越多的州正长期保留这些遗传物质,用于研究、分析及尚未公开的目的。
假使耶稣的父母是无证移民,他们与新生儿可能遭遇移民海关执法局的凌晨突袭,在缺乏实质正当程序的情况下遭拘留,经由营利性私营监狱处理,最终于深夜被驱逐至第三世界国家的拘留营。
从能够上学的年纪起,耶稣接受的教导大概就是服从政府权威,而关于自身权利的知识则少得可怜,如果有的话。倘若他胆敢在求学期间公开抨击不公,很可能会遭遇校警的电击或殴打,至少也会因学校对轻微违纪与严重过错一视同仁的零容忍政策而遭停学处分。
若12岁的耶稣失踪数小时甚至数日,他的父母必将以监护失职的罪名被铐走、逮捕并监禁。全美各地早有父母因更微不足道的"过失"被捕,比如让孩子独自去公园或在前院玩耍。
从少年时代到成年期间,耶稣的行踪与个人数据包括生物特征,非但不会从历史记载中消失,反而会被政府机构及谷歌、微软等企业记录、追踪、监控并归档。令人震惊的是,95%的学区将学生档案外包给数据管理公司,这些公司随后便利用这些数据向我们推销产品。
自耶稣与"极端分子"如施洗者约翰接触的那一刻起,他就会被标记为监控对象,只因与知名活动人士的关联,无论其是否主张和平。9·11事件后,FBI对各类活动团体展开了广泛监控与情报收集,从动物权利组织到扶贫机构,从反战团体到其他此类"极端"组织。
耶稣的反政府立场必然会被贴上国内极端分子标签。执法机构正接受培训,在与潜在极端分子接触时识别反政府极端主义迹象,这些分子往往表现出"对政府与经济即将崩溃的信念"。
在社区间游历时,耶稣可能因国土安全部的"见可疑,即举报"计划而被举报为"可疑人员"。多州已向民众提供手机应用,允许拍摄可疑活动照片并上报州情报中心,经审核后转交执法机构。
这位巡回布道者非但无法自由传教,反而可能因脱离社会体系或露宿街头而面临逮捕威胁。事实上,通过立法禁止露营、车内过夜、公共场所游荡与乞讨等方式将无家可归者定罪的城市数量已翻倍。
耶稣的教义,拒绝效忠帝国、对财富与权力的警示、坚持服从上帝有时需抵抗不公权威,在当今几乎必然被解读为意识形态极端主义。在这个异议日益被视作公共秩序威胁的时代,耶稣无需实施暴力就会被判定危险。仅其言论便已足够。
被政府视为异见分子及其权力潜在威胁的耶稣,可能遭遇过政府安插在追随者中的眼线,用以监视其活动、汇报行踪并诱使其触犯法律。这类当代"犹大”被称为线人,常因背叛行为获得政府丰厚酬金。
倘若耶稣借助互联网传播他关于和平与爱的激进主张,他的博客文章可能早已被政府间谍渗透,试图破坏其信誉、诋毁人格或在网络栽赃陷害。至少,他的网站会遭黑客攻击,电子邮件也会被监控。
若耶稣试图为大批群众分发食物,他可能因违反无许可发放食物的多项法令而面临逮捕威胁。
假使耶稣公开谈论他在荒野四十天的经历、所见异象或与邪恶势力的对抗,他很可能被贴上精神疾病标签并遭受非自愿精神病拘禁,拘留原因并非已实施的行为,而是当局担忧他可能做出的举动。当下,表达痛苦、精神信念或不顺从的行为日益被病理化,尤其当涉及无家可归或贫困状况时,更成为强制收容的理由。
毫无疑问,若耶稣试图掀翻犹太圣殿里的桌子并怒斥宗教机构的物质主义,他必将被控以仇恨罪。目前全美超过45个州及联邦政府均设有仇恨犯罪相关法律。
如果有人向警方举报耶稣可能构成威胁,他或许会被警方击毙,因为对于某些警察而言,任何被视为不服从的举动(如肌肉抽搐、提出疑问、皱眉)都可能招致他们先开枪后问话的处置。
政府官员不会派遣武装警卫在公共场所拘捕耶稣,而是会下令特警队对耶稣及其追随者发动突袭,行动中将使用震撼弹和军用装备。美国每年此类特警突袭行动超过8万次,许多毫无戒备的民众成为目标,面对这种政府暴力入侵毫无招架之力,即便突袭本身是误判所致。
耶稣若未被羁押,或许会被"消失"在秘密政府拘留中心,遭受审讯、酷刑和各种虐待。芝加哥警方就将超过7000人"消失"在霍曼广场那个未登记的秘密审讯仓库中。
以叛国罪被起诉并被贴上国内恐怖分子标签的耶稣,可能被判处在私营监狱终身监禁,被迫为企业提供奴役劳动,或通过电椅注射致命药物混合物处决。
确实,无论耶稣是诞生在他自己的时代还是我们的时代,结局很可能并无二致。一个要求服从高于良知、秩序高于仁慈、权力高于真理的政府,总会将耶稣这样的人物视为威胁。
令人不安的真相是,一个如今愿意监视、拘禁并让耶稣噤声的国家,早已背离了它所宣称尊崇的福音。
因此,圣诞节不仅是对圣婴降生的庆祝,更是对随之而来一切的铭记:伯利恒繁星之夜马槽中发生的事,只是故事的开始。那个出生在警察国家的婴孩,长大后成为了一位直面时代之恶并勇敢发声的人。
这一矛盾迫使人们不得不正视现实。
和平、正义与慈悲的事业并非始于马槽又终于某个节日,而是在颂歌声消散后仍需要长久的勇气。
这一现实与政府及其执法者日益推崇的基督教形态形成鲜明对比。一种与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对权威的服从相融合的信仰,与基督的教诲已鲜有相似之处。
此刻尤为危险的是,这种对基督教的扭曲已非边缘现象,它正日益成为主流。
现代教会在太多情况下不仅未能挑战帝国机器,反而为其施洗。当宗教领袖为无休止的战争祈福,歌颂军国主义,并将暴力描绘为神授之举时,他们实则颠倒了福音的本质。
然而耶稣并未宣扬统治、征服或屈从于帝国。他与穷人、囚徒和被遗弃者站在一起,并为此付出了生命。
正如我在《战场美国:对美国人民的战争》及其小说姊妹篇《埃里克·布莱尔日记》中明确指出的,我们必须再次做出选择:究竟要与军事帝国的机器步调一致,还是与那个生于其阴影下却敢于反抗的婴孩同行。
作者:John & Nisha Whitehead,经由拉瑟福德研究所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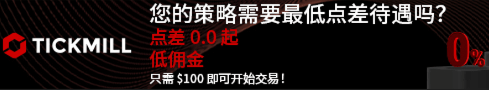 |  |